去年今天"你懂的"成经典
去年今天,吕新华以一句“你懂的”走红。

去年今天,吕新华以一句“你懂的”走红。

以前都是别人在运作,现在算是少林寺正式出场了。

记者求证确认,不少人跨洋疯抢的马桶盖,真的就是产自杭州。

简政放权这项改革进入到“啃硬骨头”的阶段。
事实证明,由此产生的良好的社会效应己逐渐显露,如国展的举办、系列丛书的出版、大型学术研讨会的举行,乃至专业书法媒体的增多,皆得力于这种前所未有的强化。目前,国内的书法爱好者过亿,这一令人咋舌的数字,也许更能说明,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是如何地深入人心。

任怀强(以下简称笔者):郑先生您好!很早就得知你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的创获,您能否谈一下其中的感受?
郑训佐先生(以下简称郑先生):不敢当,我从高邮湖畔的小县天长来到孔孟之乡的山东,深受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此耕耘三十余年,略有收获,仅此而已。
笔者:高邮曾诞生过文采诗情艺能德操俱佳的汪曾祺,没想到郑先生您出生在与之比邻的天长县。郑先生您不仅是位有口皆碑的学人,也是书坛名家。
常诚、赖非两位先生评价你的书法面貌新意叠出,或隶、或行、或章草,手追心摹,变化从心,总能让人耳目一新,总而言之,郑先生您才情高、学养深,高情雅怀只要从笔尖上稍微一抖落,便是洒金掷玉,一片辉煌。那您是怎么看待“新变”的?
郑先生:两位先生过奖了。三十年来,我坚持在传统的基础上追求新变,致力于研究前人“变化”的成功原因。我常常讲到“马蹄式”的前进:书法的新变不同于蝉蜕和羽化。书法无所谓新与旧,所谓从旧质中脱胎换骨,从旧身中蜕化新貌,新的骨肉与传统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笔者:郑先生能否具体谈一下?
郑先生:我在行书的学习上,倾心浸淫其中的人物是米芾、文征明和王铎,他们都是二王嫡传。我主张追求新变不失旧轨,容纳众美而具自家面目。我也对何绍基、金农等人开创的隶书新貌有浓厚的兴趣,我觉得学习他们,不要一味步步规模,依样画瓢,而要致力于从中探寻“所以变”的原因。
笔者:郑先生,听说近年来,您开始关注近现代出土的秦汉简帛书,您把简帛书和汉碑熔铸在一起,略掺行书笔意,使您的隶书有了一种新的面貌:沉雄中有跳宕,古雅中杂流丽。我还想倾听您谈一下书法家的素养?
郑先生:对于书法家而言,技法是非常重要的,但书法不能止于技法。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植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书法作品打动人,感染人,是因为书家的人格精神、文化品格与书法本体相互辉映:共同熔铸而成的气息。
笔者:“书者,如也。如其学也,如其才也,总之日如其人也。”在郑先生您身上,我看到了古典修养、学术造诣和诗人才情相互辉映,发而为书,自然大雅。郑先生您你能否谈一下您提倡的人文精神?
郑先生:好。我虽受到西方艺术哲学的影响,从来不轻视书法作为视觉艺术的“形式感”,但我更提倡人文精神的弘扬。由生命的感性与文化的理性熔铸而成的人文精神,对于书法家来说,这是一种宏大的精神境界。落到艺术创作中,又是一种实在美学境界。宏观的文化背景、人文精神常常是我进行书法批评的出发点。
笔者:正因为如此,郑先生,我们读您的文章,能受到震聋发聩的理论震撼,又有感到会心不远的心理契合。靳永说,“在这样的理论家面前,常常连被批评者也首俯心折”。那您是如何看待当下书法现状的?
郑先生:靳永先生过誉了。当下的书法在告别实用性的同时,又显示出一种前无古人的繁华。说书法离我们越来越远,是因为它已基本上从我们的日常书写中隐退,当下的所谓书写,因微机的全面介入,已基本蜕变成程序的输入。因此,除了从商店的牌匾上、书籍的题签上、艺术展览上,我们还能领略到书法的风采,在日常生活的其他层面,则已难觅书法的踪迹。因此有人感叹:写作俱佳的作家、学者手迹,向来被视为珠联璧合的珍藏,从今以后,这大概要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因为作为书写主体的文化工作者,已逐渐与真正的书写尤其是书法渐行渐远了。
说书法离我们越来越近,是因为它在告别实用性的同时,又显示出一种前无古人的繁华,其炙手可热的境遇甚至可以称得上“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虽说书法作为几乎唯一的书写方式,自古深受重视,如唐代就曾将之列入教育体系,并设有书法教官。但从总体上看,与当今书法显赫的境遇相比,似不可同日而语。时至今日,高等院校的书法本科专业已达百十家之多,而书法的硕士点、博士点也为数不少,乃至有人喟然生忧:如此多的书法专业人才已不是社会需求所能消化。就职业化而言,国家、省市皆设有专职画院,其中集中了一大批数量可观的书家。以上现状说明,国家已对书法这一传统的艺术门类予以足够关注,而这一关注则是当代书法事业能够踵承前代、与时俱进的最切实保障。事实证明,由此产生的良好的社会效应己逐渐显露,如国展的举办、系列丛书的出版、大型学术研讨会的举行,乃至专业书法媒体的增多,皆得力于这种前所未有的强化。目前,国内的书法爱好者过亿,这一令人咋舌的数字,也许更能说明,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是如何地深入人心。
笔者:就目前而言,无论是书法的普及推广还是书法赛事的风起云涌,仅从书法作为艺术这一角度而论,似乎隐约地让人感到一种担忧。不知郑先生你如何看待?
郑先生:当代书法繁荣的背后,的确隐伏着让人们担忧的一些问题。如体制化。它固然可以使书法创作走向有序,但引领者是否具有导向有序的理性和实力?不容否认,当代书法的引领者中不乏真正的精英人物,如舒同、启功,如仍活跃书坛的沈鹏,他们以自身的卓越文化品格向世人展示当代书法的至高境界,从而在功能上真正起到了大众表率的作用。但也有一些名实不副者,因为某种机遇而身处“领袖群伦”的位置,而自身并不具备一个设计者的素质,这些年,书法界的许多纷争,即源于这种“领袖之争”。再如学科化和专业化将书法定位为自主自为的学科和专业,并不等于削弱其必需的生长背景,但目前的状况是,书法专业被列入艺术门类的同时,也降低了文化标准,乃至高考中出现了“学习不佳学书法”的怪现象。
笔者:郑先生,你能否谈具体一下当代书坛存在误区吗?
郑先生: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这些问题。
如理性精神的失落, 在经历了经院的洗礼之后,渴望山林的朴野与跌宕;在经历了理性的约束之后,向往非理性的躁动与迷狂,这是文化史上带有普遍规律的现象。综观中国文化界的现状,无疑正面临着这样一种历史的转换。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所形成的各种文化价值正以空前之势淡化甚至瓦解,随着社会心态的变化而滋生的恍惚、散漫的浪潮,却与日俱增地弥漫于文化界的各个角落。诗人们开始舍弃传统的理想王国,把更多的笔墨泼向瞬间的感受或潜意识的流动;画家们更是怀着一种焦虑的心情,在原始艺术或其他艺术门类中寻找灵感爆发的契机。抽象、扭曲成了时髦的风尚。其表象可谓扑朔迷离,其心态可谓幽微飘渺,其情致可谓归趣难求。艺术的丰富于此可见,人们的困惑也由此而生。在这艺术的狂欢时节,书法界也扮演了狂欢者的角色。举个例子:王铎是为当代书家竭力推崇的大师,他既陶醉于艺术的狂欢中,尝受陌生化的快感,经历震颤的愉悦,又十分清醒地依恋着传统的家园。翻开他的作品集,各种临本琳琅满目,真可谓陶冶百家,然后自铸风貌。因为书法的创新不同于其他艺术,画家可以模仿自然,作家可以观照生活,唯独书法只能基本上以文字为创作的对象,而历史上的诸多名迹则是师法的最好蓝本。因此,书法的反传统、非理性常常是出入于历史的艺术回旋,横越于古今的审美体验。
再如历史批判中的困惑,随着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书法领域的又一个终结时代已经降临。这是艺术观念和价值标准都在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也是在心态是最容易陷入焦虑、彷徨的十字路口。游离家园的失落感和抛弃旧垒的冲动欲形成的强大的精神对峙,使人们一方面经历了世纪末文化凋零的痛楚,另一方面又尝受到了由新的艺术曙光的感召而产生的兴奋。前者表现为一种迫不得已然而又非进行不可的文化批判;后者经过美学的升华,可以转变为一种新的艺术形态的建构。无疑,现实赋予的双重使命,既给当今的艺术家带来了历史的荣耀,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困惑,而如何面对日渐沉沦的旧传统和负载这种旧传统的前辈书家,则成了当前艺术反思中最迫切的带有中介性的问题。正是意识到这种艺术的严峻性,当今的大部分书家和书法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他们一方面把前辈书家当作历史解剖的对象,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另一方面又以沾溉者的身份对之表现出足够的敬仰,使其艺术光华不至于因人为的扼杀而黯然失色。但不容忽视的是,也有一种不甚健康的潮流正在这种空前的文化批判中扮演着危险的角色。他们不是用历史的逻辑作为行为的规约,只是凭个人的情感的好恶进行价值判断。结果,爱之则捧于青云之上,恶之则抑于深泉之下,许多前辈书家辉煌的历史在他们轻佻甚至带有恶意的笔下顷刻间化为虚无。如说沈尹默先生的书法是“二王”的赝品,把启功先生看作“馆阁体”的余孽。凡此种种,轻则违背了历史的实情,在判断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重则艺术良心已经泯灭,流为恶意的人身攻击。对这种不顾艺术规律的武断指责,严肃的艺术家白会切齿,但对那些于艺术史涉猎不深的人们则会产生判断上的误导。
但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去考察前辈书家,更不可用今天的美学标准去苛责他们。要知道,白云苍狗而世态万变,沧海桑田而情随事迁,残酷的历史烽烟常常无情地封锁往昔的时空,斩断前后的因缘,以致在今人与前人之间形成巨大的精神鸿沟。这样,在审视过往的文化现象的时候,很容易脱离具体的文化氛围,作一厢情愿的描述和判断,提出一些悖离历史情境的遐想,认为他们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有的以所谓的“历史局限性"施舍一点悲天悯人的浅薄的关怀,有的以蛮横的现实逻辑对已经只能缄默不语者大加指责。所有这些都是价值既定的颐指气使,而不是体贴入微的历史对话。殊不知历史的轨迹是由不同时期的不同风光联缀而成的,任何一个艺术家充其量只是其中一时一处的景观,试图永葆状态,独领永恒风骚,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把这种幻想强加给前辈书家,更是梦中之梦。其实正如王羲之所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再如被消解的“权威”简单说几句西方人曾说人格即风格,中国人也说文如其人,这道破了文化品格与人格之间的渊源。历史上虽然存在文化品格与人格相谬的情形,但在大体上二者是互相补充并且统一的。对于权威而言,前者的低劣固然不能使其成为文化范式,后者的缺乏也不能引起人们的敬仰。只有二者相辅相成,才能成为一个既目光深邃又良知卓荦的文化精英。所以,权威手中唯一的利剑,应是文化法则、美学定律,而不应是其他的什么。借助于文化以外的力量以颐指气使、狐假虎威的行为,都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权威所应有的。中国自古提倡“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就是对文化精英道德上的具体规约。目前的书法热中大有借书法扬名获利者。有人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有人凭借微妙的政治背景。一些在书坛上颇有影响的人物,为情势屈,或代为作伐,或代为揄扬,严肃的艺术评判变成了无聊的逢场作戏。殊不知,正是在这逢场作戏中,一个文化权威应有的良知己悄悄泯灭,现实的艺术景观被笼罩上了一层令人悲哀的迷雾。
还有走向僵化的“书卷气” 由于特定的操作方式的限制,现代书家虽生活于当今时空,但精神的翅膀则往往翱翔于古代的氛围之中,临古代名帖,写古人诗词,发思古之幽情,可以说,无一不以古为追踪的对象,这样,其思维定势表现出一定的恋古倾向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如果处理得好,与古结缘自然可以增强自身历史的厚重感,否则,就会与时代格格不入。表现在对书卷气的理解上,参照系切不可过于局促,反之,一方面会把许多品格非常优秀但与既定的审美框架不符的书家书作排斥在外,使历史变得残缺不全;另一方面也严重地影响创作中博采众长、厚积薄发优势的形成。而对于那些以创新为宗旨的书家来说,钟情于书卷气非但不会对你的审美开拓龃龉不谐,反而会大有裨益。因为它是文化境界的象征,其功能在于显示书家人格的深度。现在一些人对书卷气采取一种弃置的态度,同样也是不明智的举动,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本质的失落。因为书家创作与一般性的书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艺术境界的营造,而这除了有赖于书卷气的作用,似乎别无选择。如果忽略了它,只能与工匠为伍了。现在不少“书家"的作品虽火药味十足,满纸硝烟弥漫,但却缺乏文化的认同感,缺乏一经寓目便徘徊不忍去的魅力,原因正于此。
笔者:那么,书家应如何避免这些呢?
郑先生:这又回到了人文精神。与文学创作界相比,当代书坛似乎更需要人文关怀。而人文关怀的重要层面大概不外乎文化和人格。说到文化层面,复杂性无过于书法。首先书法至今仍是古典性格异常凸显的文化类型,甚至可以说,没有相关古典文化的修养,很难进入其中。如一般的书法作品仍采用繁体字,书写的对象多为古典诗词、联语、格言、小品,称谓、款式也多依古制。即使自书诗词,也大多为古体。这就需要相关的知识背景。一些书家,往往在这种背景缺失的情况下率尔操觚,以致陷入窘境。
书法还是综合性或者说边缘性很强的艺术,如与之有直接关联的学科就涉及文字学、诗学、哲学等。由此看来,书法虽在传统上难免“小道”小讥,但实为“大道”。因此,历史上的许多书法大家绝不是单纯以书名世的“艺术孤岛”,而是横绝于人文领域的精英。如李叔同,对文学、佛教、戏曲、音乐皆有涉猎,书法只是其余事耳。今人如饶宗颐先生,涉及的文化领域更是令人咋舌,可谓博通今古,融贯中西。因此,书家虽盘桓于翰墨,但根扎于深广,这样方能左右逢源,允称大雅。书坛上流传着一些带有轶事色彩的佳话,其中有一类大概最为脍炙人口,即某某著名书家不以书家自居,甚至别人以此相称,他大为不悦。而一个具有艺术禀赋的人花上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可以在技法上炉火纯青,这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但要在艺术境界上达到可观的高度却绝非易事。 古人云“功夫在诗外”,书法最重要的则是边缘性的文化苦旅。
笔者:谢谢郑先生,能否用几句话作为我们这次采访的结束语?
郑先生:好,谢谢你们!唐人张聿诗云:“何处青蘋未,呈祥起远空”,我们有理由坚信正如青蘋之未可以蔚成风气,理性的沉思必然会迎来当代书坛真正的人文复归。
(任怀强,诗人,知名书画评论、策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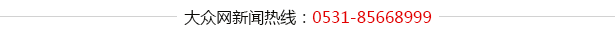
初审编辑:
责任编辑:夏莉娟